- 发布日期:2025-03-23 22:59 点击次数:84

沉香文化是与食文化、酒文化、茶文化并列的四大文化之一配资保证金,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的一块瑰宝。海上香料之路起源于古代,不同于丝绸、瓷器、茶叶等商品主要是单向输出,香料主要是双向流通。海上香路的双向流通性、香料文化的独特性,使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和人文交流更加复杂多样。
《海上香路:中国与世界》一书,历时近1年,全文13.6万字,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,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。关于这本汇集了古今中外对于海上香路与沉香文化研究的书籍,丘树宏、谢有顺两位专家给予了什么样的评价和感受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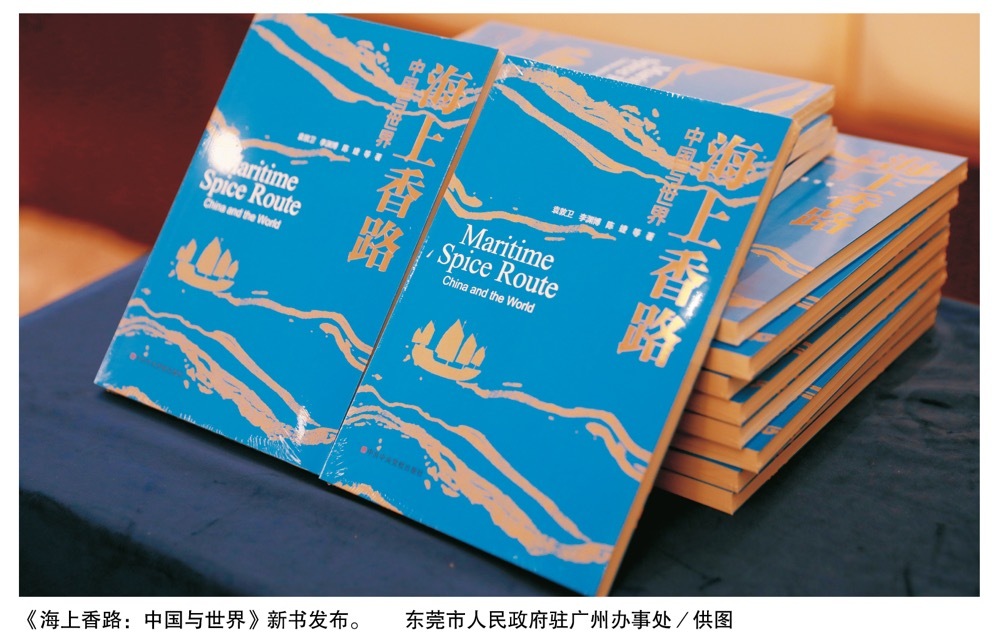
从三个维度矗立起海上香路立体形象
丘树宏
广东省文史馆馆员、广东省作协副主席
《海上香路:中国与世界》在研究海上香路方面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跨学科的研究和写作方法。作者不仅深入探讨了香料贸易的经济动因,还从文化、宗教、政治等多个角度对海上香路进行全面剖析。这种跨学科的方式,使读者能更全面、更深入地理解海上香路的历史意义和影响。时空经纬(人类性)、考据佐证(学术性)、散文笔法(文化性),“三性”合一,是我阅读这部著作最深刻的印象。
一、时空经纬,贯穿人类发展史
通过阅读《海上香路:中国与世界》,我们对海上香路的历史背景有了全面的了解。海上香料之路起源于古代,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东西方贸易的繁荣,逐渐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贸易通道。它不仅促进了商品和文化的交流,还推动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。了解这一历史背景,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海上香路的历史意义和现代影响。
中国香料从海上走向世界,异域香料从海上涌向东方。以“香”的名义,《海上香路:中国与世界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互为交叉、贯穿,将数千年的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勾连起来,让读者获得了历史厚重感和现场感。
二、考据佐证,筑起学术博物馆
《海上香路:中国与世界》的描述对象,一是香料本身,包括香料的制作、香料的用途等;二是香料的交流和影响。这两个方面,作者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。作者引经据典,用了大量文字来证明货单的真实性。可见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,更给后人还原了重要的历史真相。
比如这一段——澳门:广州的“外港”。船队由果阿(今印度一邦)去柯钦(今印度西南岸),以便购买香料和宝石,再从那里驶向满剌加(今马六甲),购买其他品种的香料,再从巽他群岛购买檀香木。然后,船队在澳门将货物卖掉,买进丝绸,再将这些连同剩余的货物一起在日本卖掉,换取金银锭。葡萄牙历史学家徐萨斯描述的是东西贸易的一条完整链条,在这一链条中,澳门的贸易地位至关重要。明正德九年(1514年),葡萄牙人开始来华贸易。16世纪初期,葡萄牙人占领满剌加后,首先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手里夺取了对印度洋贸易的控制权,并逐步向南洋群岛方向扩张其海上势力。1620—1644年间,明朝统治者与关外的满族人进行战争,需要大批武器。葡萄牙人抓住机遇,向明廷提供军火,带动了澳门的经济。1757年,随着广州“一口通商”政策和商业优势确立,澳门在中外贸易中的有利地位更加凸显。但凡到广东从事贸易的船只,必须先将船舶停靠于澳门,待粤海关核准后,方能进入广州内河贸易。因此,澳门表面上独立于广州,实际上是广州的“外港”。为了说明澳门成为广州“外港”,作者不厌其烦地提供了非常翔实的证据,让读者读来印象深刻,信任感极强。引经据典、旁征博引、孜孜以求的学术性,让《海上香路:中国与世界》俨然成为海上香路的立体博物馆。
三、散文笔法,洋溢文化大气场
《海上香路:中国与世界》突破了以往某些海上丝路主题的学术著作套用呆板、生硬的框架,而尽量用散文化的笔法表达严肃的历史事实。比如标题的设计:《海上香路,中国与世界的“香交”》《一缕平安香,半部中华史》《海上来香:异域香料与华夏的相遇》……几乎所有的大小标题,都显得诗意流淌,韵味十足。
“畦留夷与揭车兮,杂杜衡与芳芷。”(屈原《离骚》)“留夷”“揭车”“杜衡”“芳芷”都是香草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使用众多香草香木来比喻人的美好品德和高洁志向。海上香路,通过香料贸易为感官提供愉悦,为心灵提供疗愈,提升人类生活品质,而且也联通了中国与世界,透过香味把世界联为一个可以相互理解、彼此认同的整体。
时空描绘人类历史,这是该书的核心;考据佐证描绘学术理论,这是该书的支撑;散文笔法描绘文化氛围,这是该书的灵魂。而这三者互为彰显、高度融会,则矗立起了海上香路的立体形象。
《海上香路:中国与世界》对当今海上香路以至整个丝绸之路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启示。它提醒我们,在研究历史时,不仅要关注经济因素,还要重视文化、宗教。
发现嗅觉里的岭南
谢有顺
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在视听觉之外,发现一个嗅觉里的岭南,似乎更符合岭南的特性,因为无论从地理条件、物产资源还是人文内涵上看,岭南都蕴藏着不可取代的嗅觉文化富矿。
《海上香路:中国与世界》对岭南沉香的描述收放自如,富有变化,比如书中第149~150页写海南沉香曾被誉为“琼脂天香”,是我国历史悠久的高品质沉香。明代名医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:“香之良者,惟在琼、崖……占城(越南)不若真腊(柬埔寨),真腊不若海南黎峒。黎峒又以万安黎母山东峒者,冠绝天下,谓之海南沉,一片万钱。”
其实李时珍对岭南沉香的评价并非凭空而来,而是引述了蔡京的儿子蔡绦的话,蔡绦曾被流放岭南白州(今广西博白一带),对岭南沉香情有独钟。他说,论沉香,“占城国(今越南境内)则不若真腊国(今柬埔寨境内),真腊国则不若海南,诸黎洞又皆不若万安、吉阳两军之间黎母山。至是为冠绝天下之香,无能及之矣……海南真水沉,一星直(通‘值’)一万”。
紧接上文,书中还写道:“目前,海南乐东、昌江、儋州、屯昌、琼海等地均有人工栽培的白木香。海南沉香因其独特的香气和药用价值而闻名,形态特征也较为独特,如黑油格多呈黑褐色,中有浅黄色相间,斑纹呈不规则片状或团状,毛孔为点状。”这一段落既呈现了人文历史,又陈述了产业现状,还描述了沉香的形态、颜色、气味,表现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和文字功底。
此外,《海上香路:中国与世界》还以线带面,生动呈现了许多与香有关的历史节点。唐天宝七年(748年)春,鉴真应日本僧人荣睿、普照之请,“造舟、买香药、备办百物”,从扬州启航,试图第五次东渡。不料在海上遭遇大风暴,共载有35人的海船一路向东南漂流,于冬季漂至海南振州(今三亚一带)才得上岸。
海南万安州首领冯若芳热情迎接鉴真一行,“请住其家,三日供养”。冯氏势大财雄,会客时“常用乳头香为灯烛,一烧一百余斤”。宅院后面,名贵苏木露天堆放如山。而冯若芳和冯盎一样,也是冯宝、冼夫人的子孙。其实,无论是乳头香、苏木,还是冯若芳后来布施给鉴真东渡僧团的益智子(一种姜科香料)、香橼(一种芸香科香料)、荜拨(一种胡椒科香料)等,并非都是本土物产,大多是岭南发展海上贸易的结果。意味更深的是,鉴真第二次和第五次东渡前在扬州药市采买的香药,与他在海南目见鼻闻的香药多有相似:沉香、胆唐香、荜拨……似乎说明海南与扬州的香药市场相仿,已然显露出几分贸易全球化的迹象。
这两处香药市场一南一北,由鉴真大师奇妙地串联起来,这样的遇合至今仍是唐代南北交流史和中日交流史上的高光时刻。扬州、海南的香药市场之所以显露出相似的全球化迹象,是因为它们都是唐代海上贸易中各国商船可以直达的港口。海上香路与海上丝路、海上茶路、海上瓷路一样,都需要被重新发现,就像嗅觉里的岭南需要被重新发现一样。因为发现一个嗅觉里的岭南,也意味着发现一个以嗅觉联通的中国与世界。
发现嗅觉里的岭南,是一项具有创新价值的基础学术工程。袁敦卫、李渊博、陈婕等岭南学者撰写的《海上香路:中国与世界》一书,就是对这项创新工程的积极回应和精彩演绎。全书取例精当,线索简明,放眼中外,勾连古今;宏观与微观穿插错落,主要史实与嗅觉审美、视觉审美交错呈现,体现了该团队的学术功底和大众传播的匠心,值得有兴趣的读者开卷一读。
【文字整理】 李梦醒
【本文责编】张蓓蕾
【频道编辑】陈地杰 李卓华
【文字校对】潘经春
【值班主编】张蓓蕾 郭芳
【文章来源】《南方》杂志2025年第1、2期合刊


